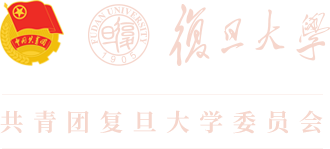玩火也玩得漂亮:蔡国强的远行与归来
2021-11-2320:30
从北京奥运会开幕式上走过京城中轴线的29个烟火大脚印,到连接地平与银河的焰火天梯,再到国庆70周年庆典的「长青大树」和「孔雀开屏」,艺术家蔡国强不断追逐爆裂、追逐火光,开启了一个极具冲击力的、刹那与永恒并存的绚烂世界。
近日,蔡国强《远行与归来》个展在浦东美术馆展出,又一次将这位爆破艺术家带回国内大众视野。《复旦青年》特邀视觉文化专家高燕老师,带领我们走近蔡国强,深入了解这位「烟火诗人」的远行与归来。
高燕
复旦大学艺术教育中心副教授
研究方向为文艺美学、视觉文化、影视美学
复旦青年记者谢雨桐 报道
复旦青年记者谢雨桐 主笔
复旦青年记者陈佳月 顾然 编辑
![]()

▲北京奥运会开幕式上的烟火大脚印
烟火诗人的诞生
在本次展览四楼「媒材的远行」展厅,有一件非蔡国强的作品,那是父亲蔡瑞钦画的火柴盒。
1957年,蔡国强出生在福建省泉州市一个小渔村。在童年的记忆里,家里总是往来着泉州几乎所有爱画画的人。父亲蔡瑞钦不但是小城的书店管理员,更是一位小有名气的书法家和传统画家。在儿子的记忆里,蔡瑞钦总是温和慈爱的,时常抱着幼子在膝上卷纸烟,他自己则在火柴盒上画山水。
多年来,父亲描画的火柴盒一直被蔡国强带在身上。「我问他画的是什么,父亲都会说画的是家乡。等我慢慢长大后发现,家乡的渔村根本就不是他画的样子,树很小,海湾很小,也只有几条小帆船,但他在火柴盒上每次都画高山流水,很多大帆船,其实他是通过一个小小的火柴盒描述他对故乡的情感和意境,对大自然的情怀。」蔡国强追忆道。
在父亲的引导下,蔡国强走上了艺术道路,很快他收获了第一个粉丝和专属收藏家——他的奶奶。奶奶对他的每一张画作都会珍而重之地保存,对他父亲的画却嗤之以鼻,认为蔡父从不将赚到的钱带回家,这种行为对一个家庭的长子而言「不可饶恕」。
蔡国强在忆及这件事情时解释道,父亲赚来的钱全部用来买了书,将书视为留给儿子的财富,但这些财富在“文革”期间被迫烧掉了,当时蔡父每天要烧书四小时,为了尽快把书烧完,年幼的蔡国强也会来帮忙。燃烧的书籍、疲惫灰心的艺术家父亲和沉重的家庭责任构成了蔡国强最初的自我冲突,艺术与现实间的矛盾内化成他的人格构成,渗透进了他后续的创作中。
![]()

▲蔡国强(左上)全家福
在蔡国强的印象里,泉州是一个「迷信」的地方。那里宗教混杂,工艺发达,自由多元,有着当时社会斗争风浪吹不到的死角,艺术就在这样的氛围下蓬勃发展着。
泉州的两座石塔是蔡国强对「迷信」的最初认知。据说在宋朝年间,泉州因为发展得很差,就去找风水师来勘验地势,风水师说,旁边山上比它更高的城市规划得像渔网,而泉州地形如鱼,被困在「渔网」之中,须得造塔破了「网」才能挽救颓势。蔡国强在这个相信风水和玄学的城市长大,作品也就总带有追寻「不可知力量」的意味。
家乡对烟火的重视,成为蔡国强艺术载体的灵感之源。泉州人的每一个重大场合都离不开烟花爆竹,婚丧嫁娶,节日乔迁,烟火就像城镇的哨兵,宣告着事件的发生。火药在这里有着非同一般的神圣地位,蔡国强在烟火的爆炸声中成为自己、解放自己,他表示,家乡是他艺术形式的起源,也是他的最终归宿。
长大后,蔡国强外出求学,上海是他这艘小船漂泊他乡的第一个港口。1978年,他首次离开泉州,乘着煤车来上海看「法国十九世纪农村风景画」展览,这是他第一次亲眼看到外国人的原作,也是他第一次知道莫奈、毕沙罗等艺术家。「原来每个人都是很不一样的,你没必要画得很像。」蔡国强回忆道。
80年代初,蔡国强来到上海学习舞台设计。虽然没能进入美院,但是上海戏剧学院一样开阔了他的思维和想象。在当时「伤痕美术」的冲击下,中国当代艺术开始各显神通,各种西方艺术流派也与中国的艺术思潮交汇碰撞。蔡国强在这样的氛围和上海求新求变的城市精神中进一步学习,明白了「原来艺术是不受限制的,艺术是可以放开的」,他也自此开始寻求对传统创作的突破和反抗。
「蔡国强本人的艺术创作经历可以为我们提供一个很好的窗口,让我们去理解和审视当代艺术中的跨文化性质。」高燕指出,蔡国强成长于传统中,学习于体制内,却试图反抗传统和体制的限制。但这种反抗始终囿于东西二分、东西对立这一集体意识形态的框架中,当时的文化取向十分单一,非此即彼,这让他的反抗既无法真正摆脱传统,也难以深入实现自我表达。
1986年,蔡国强在上戏毕业一年后,远赴东京留学。在日本学习和定居期间,蔡国强接触到日本文化,发现日本艺术从古代中国吸取了很多东西,在现代化的进程中,这些传统的内容没有被视为落后与腐朽遭到抛弃,而是作为民族文化认同的内核被赋予现代美学形态,获得了与西方对接的现代性表达。
于是,在日本——这一东西文化交汇前沿的语境中,蔡国强融合中西,在作品中表达出跨文化的观念碰撞。他不但重访东方艺术传统,也注意从西方底蕴中汲取营养。凭借《草船借箭》《撞墙》等作品,他在东西方艺术世界都声誉卓著。在世界弥漫着沙文主义的猜忌与不安之时,蔡国强却能「把全人类的文化遗产作为自己的文化遗产,把不同文化的先辈都作为自己的先辈去尊重。」
![]()

▲《草船借箭》
正如高燕强调的,至此,蔡国强发现了超越一切二元对立框架的可能性,从容地在各种文化传统中汲取对自己有益的内容。他创作的「外星人系列」将触角跨过政治和文化的界限一直延伸到地球之外的宇宙,试图用纯粹的艺术表达去创造基于世界大同的人类共同语。通过不断重审自己与艺术史的关系,蔡国强得以自由地在不同文化传统中穿梭,其作品展现出了惊人的超文化能力,最终为不同的观众接受而走向世界舞台。
刹那含永劫
看烟火时,我们在看什么?
人类用烟火把美丽的星云安置在眼前,看其中的白矮星慢慢冷却,演变为永续死亡的黑矮星。当一颗礼花弹归于虚无,另一颗便接着蹿起,散成满天星,然后一颗接一颗,前仆后继,像生命一样,有时候眼泪就流了出来。
![]()

▲烟花现场
一千多年前,中国人研究火药,是希望得到长生不老之方。因为在研究时,调制的药会炸开,便取名「火药」。「慢慢地,中国人就把这项研究用在了欢乐的事上,它们创造了很多美好的夜晚。」蔡国强在他的纪录片里娓娓道来。他就从这美好的物质中吸取力量,并将它作为一种崭新的艺术材料引入创作。
![]()

▲《黑火NO.1》
在「远行与归来」的展厅墙壁上印有这样一段话:
即使有些东西是永恒的,你也无法永远拥有它。永恒和永远在中文里是不同的。永恒是超越时间的存在,而永远存在于时间中。所以当我们通过艺术与永恒对话、与它相连,我不会试图从永远的角度去应对,而是用瞬间去把握——似乎只有在混沌的片刻才能品尝到永恒的神秘。
某些材料的性质决定了一件作品可以在物理层面永久留存,这是「永远」;而「永恒」则是在精神性的维度。刹那烟火无法达成「永远」,但却可以达成「永恒」。刹那与永恒、破坏与重建——在二元对立中,烟花可以说是一种近乎完美的表达形式。
如海德格尔所言,永恒或瞬间与客观意义上时间持存的长短并不相关,与之相关的只有艺术中真理的发生。艺术总是在显现真理的短暂一瞬实现它的永恒。正如火药爆破的一瞬间,存在之真理从存在之物的遮蔽中绽出,人们的感受也于这一瞬从心底一起迸发出来。瞬间的喜悦、孤独、悲伤一同被火光照亮,人就这样在喧嚣中得到宁静,在刹那中获得永恒。
生命流逝,无人能够追及时间之轮,但生命也正是因其短暂而不断追寻着价值的缔造。世界流变、生死相续、能量守恒,宇宙处于无目的的不断进行的永恒轮回中。尼采所谓的“酒神状态”,便是人类自我与宇宙万物合而为一、息息相通的状态,既肯定人的痛苦,又肯定人的欢乐,生命由此获得解脱与安慰,并敢于承担起自身的意义。
对蔡国强而言,这也是生命的本质:相较于看似漫长实则刹那的一生,或许我们对宇宙万物循环往复的切实感受,才是真正的永恒。

![]()
▲《乌菲齐研究:花神第三号》
关于「天梯」的梦
宇宙是否有尽头?生命的意义何在?作为人群中最具敏感性和想象力的代表,艺术家在人类追寻真理的过程中尤其重要。
艺术,是蔡国强去往宇宙的时空隧道。他期待一种对话,一种过程与来往。几十年来,银河都是他的永恒之乡。在「远行与归来」的中央展厅——这个在全世界美术馆中都少见的高30余米,长、宽各17米的空间中,蔡国强注入了他的宇宙观,打造了特别委任项目——奇观装置《与未知的相遇》。
这是时隔七年,蔡国强再次回到上海的力作。狭高的空间里,流转着眩目的光晕,他以超越线性历史叙事的方式,大量运用白色、蓝色、紫色的灯光呈现一个少年的宇宙光华。在他眼里,灯光虽然无法代替烟花的效果,但也自有其魅力,白光看起来像艺术家的素描世界,紫色看起来有神秘的宇宙感。
飞碟、外星人、升天的古人万户、米开朗琪罗的《创世纪》……从地下仰望,光影向人倾泄而来,在旋转的飞船、宇航员、鸟构造成的奇异斑斓的时空隧道前,观者仿佛立于洪荒入口,不知今夕何夕;从楼上平视,又会让人收获莫名的感动与浪漫,如同贴近了无数人类在短暂人生中对宇宙执着追寻所构成的漫长历史,早期形象与未来想象融通在一起,泛着灵动又浪漫的烟火气。
![]()

▲《与未知的相遇》
蔡国强对宇宙有着热烈而绵长的向往。
「很早的时候,人们就想象着,只要找到一只大鸟就可以来到太空。人类在漫长历史中不断有离开地球的想法,这些都是很好的人类少年宇宙船,这些精神不会因为我们已经到了火星就不需要讨论,人类对宇宙的情感和对生命故乡的情怀永远没变。」
1969年,蔡国强看到阿姆斯特朗登上月球,迈出人类走向宇宙的重大一步时,无边的喜悦和失落同时击中了他。他喜悦于人类在走向宇宙,又为自己永远无法踏入太空而深深落寞。
「我感到我未来不可能去宇宙,我挺伤心的,但我慢慢理解了。」
对于大多数人而言,「理解」意味着认清现实,放弃幻想,但极度浪漫的蔡国强不会停下来。他经常想做一个梯子,伸进云层,但这个梯子不是为了带他去宇宙,而是为了带他奔赴一场他期待已久的对话。「这是一架通天的梯子,就像基督徒试图更靠近上帝一样。我们要做一架梯子,把这个城镇和外太空联系起来。」
这个关于「天梯」的梦,蔡国强一做就是二十一年。
1994年,在英国宇航局的支持下,蔡国强首次尝试制作天梯。他希望利用热气球把装满导火线和火药的梯子拉上天空,但由于当地恶劣的天气条件,最终没能实现。2001年,在上海APEC会议期间,蔡国强再次试图实现天梯的愿景,但因为「9·11」事件的影响,计划再次搁浅。十年后在洛杉矶,他设想天梯从葛瑞菲斯天文台升起,方案获得了官方的批准,但未能获得当地居民的一致同意,最终也未能实施——现实的壁垒比「天梯」更高更重。
二十一年来连续的失败,仿佛是上天在嘲弄蔡国强的渺小与妄为。当被问及为什么这么多年一直坚持为天梯奔走时,蔡国强说:「我想把天,烧给奶奶看。」
那架连接大地和天空的梯子,曾一次次被孩提时代的蔡国强绘在纸面上。那时,奶奶是家里的顶梁柱,对这个孙子关怀备至,并且认定:她的孙子将来一定是不得了的艺术家。奶奶的鼓励坚定了蔡国强的信心,他一定要把天梯从稚拙的水彩画带到人间,给奶奶放一场天底下最完美的烟火。
所以,这个天梯梦,还得做下去。

▲蔡国强和奶奶
造一座人间「巴别塔」
2015年6月15日的凌晨4点49分,历经21年波折后,蔡国强终于「拧过了上帝的大腿」,在自己的老家泉州架起了一座宽5.5米,高500米,连接天空和大地的焰火天梯。
他最初把这件作品选址在自己长大的渔村,但过度开发的渔村已失去了其本应具备的「神奇感」。于是他转而选址惠屿岛——这个他认为最像渔港的渔港。蔡国强认为,尽管他从全国带来了自己的朋友,有最好的汽艇驾驶员、最好的技术总监、最好的烟火师,但这个岛上的人,配得上全中国最好的。
在他眼里,惠屿岛有灵性。不是每个渔港都能有灵性的,这和人有关。
纪录片《天梯:蔡国强的艺术》中记录了天梯诞生的一刻。蔡国强点燃引线前,神情平静得像月光下的大海,周遭吵嚷嘈杂,更衬得他通身祥和安静。他双手合十,开始祈祷,没人知道他在想什么,在与谁对话,但那虔诚的一瞬,让任何一位无神论者都愿意相信神明的存在。
用香点燃引线,是蔡国强的仪式感。在点燃的刹那,他的神情瞬间松弛下来。从此,他已然得「道」,除了他的烟火,一切都不再重要。
天梯自下而上一段段爆燃,灼烧,借着热气球的力量一节节爬升到500米的高空,直至宇宙。此刻的烟火不再是民间的娱乐,而变幻成人类共同的语言,以一种近乎神性的形式,搭建起一座通向宇宙的当代「巴别塔」。
![]()

▲隔着屏幕依旧震撼人心的天梯
「真是太漂亮了。」蔡国强淡淡地说。他的妻子倚着一根电线杆,满脸是泪。蔡国强轻轻抚着她的背,递过一张纸巾,通天之梯在他们身后点燃了夜空。
![]()

▲现场的蔡国强和妻子
这时,蔡国强的奶奶已经100岁了,因为身体无法负荷,她并没有到现场,而是通过视频通话观看了这个为她而作的壮举。在视频的这边,她看见一架焰火天梯腾空而起,年近花甲的孙子笑着对自己说:「阿嬷,漂亮吗?你孙子是不是很厉害?」
一个月后,老人安详离世。
![]()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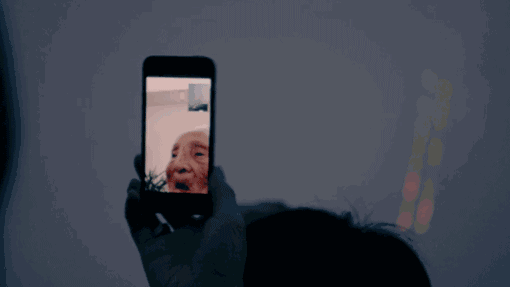
▲蔡国强在天梯现场连线奶奶
人类耗尽一生是为了什么?我们在完成什么,又在消灭什么?蔡国强用150秒的壮丽与绚烂回答了这些问题。他没有辜负自己少年时摸云摘星的梦想,也终于回归到那个给予他血肉的地方。只是不知他那一刻,有没有收到另一种他一直期盼的声音,来自一个更宏大的世界。
不过收到与否都没有关系。至少,漆黑的宇宙总是在为人类送来明亮的流星,而在天梯燃烧的那一刻,终于有地球上的人,将流星的光芒也送去了宇宙,作为真诚的回礼。
图片来源于网络
微信编辑丨陈佳月
审核丨甲干初